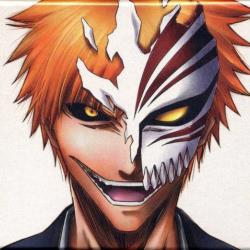
先秦的时候,墨家曾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派别。孟子曾经感 叹“天下之言,不归杨,即归墨”,并且以“口距杨墨”自 任。到了韩非子著《显学》的时候,他说: “世之显学,儒、 墨也”。《吕氏春秋.当染篇》则把孔、墨并举,说“举天 下之显荣者,必称此二士(孔、墨)也—–孔、墨之后学, 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但是,等到司马迁写《史 记》的时候,居然无法为墨子作传,只在《孟子荀卿列传》 中附了一段小文章: “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 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除此以外就没有什么记述。 汉朝早期的时候,墨子仍然被视为智慧的代表,与孔子并称, 比如《史记.李斯列传》中说: “必有乔松之寿,孔墨之智”, 《淮南子.主术训》中说: “吴起、张仪,智不若孔墨”。 但是自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墨子似乎就从思想界消失 了。直到清朝的重新校注《墨子》,二千年间,只有韩愈等 一两个人曾经说过同情墨子的话,至于注解的人就只有晋朝 的鲁胜一人。
这种现象难道不是非常特别吗?譬如大地上原来有两条河 流,几百年后,其中一条干涸了,人们只习惯到剩下的那一 条去取水,于是,他们说:天下的水都必须从这条河中去取。 假如墨子的思想是无益的,那么,它的衰微就没有什么可以 感叹;假如这条河流的水是不可饮用的、无法通行的,那么 它被堵塞,就没有什么可以感叹。但是,如果它的断绝只是 由于人们的疏忽、无知与偏见,那么,当人们发现它的遗迹 的时候,就会感到非常遗憾。历史并不是成王败寇的舞台, 从泥土中挖出来的古希腊雕塑的碎片,其价值要远高于教堂 的闪闪发光的镶玻璃。今天,当人们去审视墨子所遗留下来 的思想时,不免会有同样的感慨。
一辈子饮用黄河水的人,他们也许会说:中国的水是浊的, 他们也许会觉得饮浊水就是他们的命。但是,如果他们了解 更多源头,就会说:这不过是历史的成迹,并不是必然性。 对于中国文化,人们观其成迹,已经发过许多议论,但是, 那些想要把那些特点作为中国文化的天性的人,如果他们了 解更多早期的生动活泼的思想,就会觉得自己的判断过于武 断。我们马上就可以用墨子的思想来揭示这一类谬误。
述而且作
保守性是人们所认为的中国文化显示出来的一个特点。这种 特性的源头,就是孔子所说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但 是,墨子早就明确反对这种态度,他把“述而不作”看做“甚 不君子”者的一种。在《耕柱》篇中,他说: “吾以为古之 善者则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老子说“知 止不殆”,《大学》中说“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 但是墨子告诉我们“善”是可以“益多”的,这是中国最早 的“进步主义”。
方法的自觉
论述的直觉性、辩论的独断,也是中国文化显示出来的一个 特点。就以孟子攻击墨子的话作为例子,他说“杨氏为我, 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这句话作为他的感情的表达则可,作为分析则不可,因为他 实际上是故意扭曲了墨子的主张,并以此作进一步的夸张。 后来,这种道德化的独断方法竟成为中国人辩论的一个习 惯。反过来看墨子,他对待儒家的态度则是分析的,在《公 孟》一篇中他说儒有“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程子觉得他过 于严厉,他说: “儒固无此四政者,而我言之,则是毁也; 儒固有此四政者,而我言之,则非毁也,告闻也”。他对孔 子也是分析的,他曾经引用孔子,别人问他为什么非儒而又 引用孔子的话,他说: “是亦当而不可易者”。重视分析的 态度是中国后来缺乏的,儒、道讲道理,多是启发性、论断 性的,所以,《论语》里面很多概念的含义研究了几千年至 今都不清楚。这样的传授方法永远都必须要权威,必须依靠 权威来解释,这种方法是扼杀学生的独立性的,只有你把自 己变成权威之后你才有独立性。人们常说中国人缺乏个性, 也许根本上就是这个文化后来的传授造成的,因为在那里方 法是隐藏的、随意的、无法明白地告诉学生的。但是,墨子 则不然,他为研究问题确立了“三表”,就是“有本之者, 有原之者,有用之者”(《非命上》),“本”是历史,“原” 是诉诸百姓耳目之实,“用”就是付诸实施以观察后果。《墨 子》一书中“三表”的应用比比皆是,对许多问题都是按这 些原则去分析的。“三表”的确立和运用本身是一大贡献, 但是,更伟大的贡献是意识到必须为研究问题确立方法,因 为只有有了方法的自觉,才可能有研究的活动。后来在中国 的学术中真正可以说是研究的,其实微乎其微。墨子还提出 “察类”与“明故”的原则,“察类”就是概念的明确性, “明故”就是因果性,通过探寻概念的含义和因果性来研究 问题,这不就是“苏格拉底式”的“辩证法”吗?这一类问 答在在《墨子》一书中也是随处可见的,在那里我们可以看 到与古希腊哲学家一样的思想光芒。
逻辑与实验
爱恩斯坦曾经推测科学是很难在中国产生的,因为科学依靠 “逻辑与实验”,而这两者是中国传统所缺乏的。但是,如 果他了解墨子的思想,他的说法就会不一样,因为在那里已 经具备相当全面的“逻辑与实验”的思想。墨子的科学思想 最集中地体现在《墨经》以及《大取》、《小取》之中,其 中不但已经有纯科学(比如试图对数学的基本概念“平、中、 厚、圆、方”进行定义、试图对时空结构进行定义),而且 已经对科学的方法论进行探讨(诸如对充分、必要、充要条 件的研究,对辩论、推理方法的研究)。这几篇文章也许在 完备性上还是比一个世纪后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逊色, 但是就它们在思想中引入了这种自觉性而言,它们是与亚里 士多德的著作一样伟大的,如果考虑到由于长期的忽视,这 一部分内容肯定有散失和模糊,这种评价就更有根据了。观 察与实验也已经被有意识地进行了,诸如在光学、力学上的 成就,墨子本人不但以“巧匠”闻名,在他的书中还留下了 机械设备的发明。在这一切之上,也许更重要的是,墨子把 这部分内容作为他教授学生的重要内容。因此,正如李绍崑 先生说的“(墨子)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发明家,而且即使 不是中国古代唯一的最伟大的科学教育家,也是最伟大的科 学教育家之一”。而这一传统的衰微直至长期断绝,的确是 中国科学史中最不幸的事件之一。
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到这里,我们还没有谈到墨子思想中最伟大的部分,还没有 谈到他的“兼爱”、“非攻”的伟大理想,还没有谈到他对 宿命论的猛烈攻击,还没有谈到他“急义”、“苦行”的伟 大人格。他的理想社会是一个“上尊天,中事鬼神,下爱人” 的社会,他认为父母、老师、君主都不是道德的最高权威, 因此,他要讲“天志”、“明鬼”,但正象詹剑峰先生说的 “他的思想和活动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是此岸的,不是 彼岸的”。从墨子开始讲学的时候起,就有人攻击他的政治 观念、道德观念,但是,却几乎没有人怀疑过他的人格。《淮 南子.修务训》中说: “孔子无黔突,墨子无暖席。非以贪 禄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万民之害”。他是中国历史上 最伟大的人格之一。
梁启超先生对二十世纪重新重视、研究墨子贡献很大,他在 《墨子之论理学》中说: “以全世界论理学一大祖师,而二 千年来,莫或知之,莫或述之”,这使他非常感慨。历史如 果是由思想的辩论来决定的话,那么墨子必定不逊于孔子, 墨学在中国历史上一度长期断绝一定是理论之外的原因。探 究这种原因,或者去探究历史的可能,也许是很有意义的。 但是,更重要的是,认识这一遗失的传统是认识我们的文化 必不可少的一环,历史即是我们的集体自我意识,我们不能 再在这个问题上采用独断论的方法了。 注:对于《墨子》一 书的著作情况尚有争论,本文基本上采用詹剑峰的说法,把 《墨经》视为墨子自己的作品,而把《十论》视为墨家学者 所记录。
作品来源:鲁山文学艺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