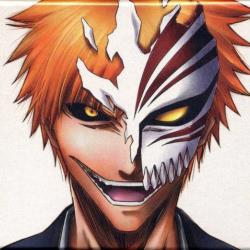
在近几年的文物工作中,通过对墨子里籍的调查及对其思想的研究,发现鲁 山境内有多处“劝善居”等形式的“劝善”组织。多数叫“劝善居”,也有叫“成 义堂”的。不管名姓怎么叫,细究这些组织的讲学内容都与墨子的原著有关。这 些“劝善”组织的宗旨均是为了聚众劝学,教人为义行善,用因果报应的“明鬼” 故事来说服人们。
《墨子》原著中有一百三十多处善民、善者、为善、闻善、善言、善行、 不善、劝善、善人等。墨子原著中的“善”字与鲁山境内的“劝善”组织的 用语及人物称呼相吻合,是不是巧合?通过走访调査,发现不是巧合,而是 一种思想源流的延续,是墨子后学组织的发展。这些可以从墨子的教学目的 到“劝善”组织的宗旨;从墨子对“义”的评价到“劝善”组织行义的实践; 从墨子的教育原则到“劝善”组织的因人施教;从墨子的强教强学到“劝善” 组织的设堂讲学;从《墨子》原著中的习惯用语到“劝善”组织的宣传用语; 老百姓对其组织成员的称呼等等方面,都足以说明鲁山境内的“劝善”组织 与墨子有着密切的关系
为什么墨子要坚持“有道者劝以教人”呢?这是他认识到教育人的重要意义 和作用。在墨子看来,自己的主义是“有力以助人,有财以分人”(《鲁问》)。同 时,他也已经认识到个人的力量有限,“翟虑耕而食天下之人矣,盛然后当一农 之耕;分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籍而以为得一升粟,其不能饱天下之饥者, 既可睹矣”(《鲁问》)。如果仅靠自己的耕种收获来养活天下之人,那只能相当于 一个农夫的作用。用来分给天下,一个人分不到一升粮食,就算每人分到一升, 也不能使饥者得饱。同样,自己一个人纺织或从军,亦“不能暖天下之寒者”, 抵挡不住“敌军”之众的侵略。因此,他才毫不犹豫地从事了为义劝学的政治宣 传活动。
他在《鲁问》篇中说:“翟以为不若诵先王之道,而求其说,通圣人之言, 而察其辞,上说王公大人,次说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国必治;匹夫 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故翟以为虽不耕而食饥,不织而衣寒,功贤于耕而食 之,织而衣之者也。”
鲁山的“劝善”组织都是以宣扬墨子的《墨经》为主,他们在农村春季庙会 期间务必赶会,聚众宣传。平时庙会少,不定时的在集市街口设起用木板搭的临 时台子,一个“善人”(是“劝善居”的教师),手捧《墨经》书本,接连宣读、 讲解,以强力讲学劝善。
瀼河乡瀼东村的村民刘丙臣(现年 83 年),在回忆当年的教学情况时说:“我 们称讲学劝善的人为先生,外边老百姓都称这些先生为善人。他们逢庙会,逢集 时就不错过机会,在会上、集上设台念《墨经》,平时不赶庙会时,他们让我推 着独轮车,带着布篷及赶会宣传的用具去各村宣传,在不外出讲学时,每天都有 许多人来到,听先生们诵经说书”。
鲁山的“劝善”组织在建国以前是有活动的。他们的诵经用语基本在《墨子》 原著中都能找到,老百姓对这些组织的称呼也能在《墨子》原著中找到原话、原 意。如称“成义堂”、“劝善居”等组织的教学活动为“劝善”,称讲道人是“善 人”,称听道是“闻善”,说《经典》的内容是“善言”,说人们做好事是“善行” 等等。我们通过细访重查,越研究越认为两者联系密切,将这些情况归纳如下:
在墨子原著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墨子对“善”的认识和对“善”字的应用也 有个过程。
在《尚贤》中篇是这样论述的: “……古者国君诸侯之不可以不执善,承嗣辅佐也,譬之犹执热之有濯也, 将休其手焉。
“……若有美善,则归之上,是以美善在上,而所怨谤在下,宁乐在君,而 忧戚在臣”。
在《尚同》中篇又连续出现了“善者”、“闻善”、“善言”、“善行”、“劝善”、 “善人”等词句。
有关“善言”的词句有“……去尔不善言,学乡长之善言;去尔不善行,学 乡长之善行。”“……去尔不善言,学国君之善言;去尔不善行,学国君之善行。” “……去尔不善言,学天子之善言;去尔不善行,学天子之善行。天子者,固天 下之仁人也。”
从这些词句可以看出墨子是用教育的手段劝说世人,以乡长、国君、天子的 好言善语教化人们,并且又强调了天子、国君、乡长要自己以身作则的善行影响 带动人民的行为,使之去掉不善的言论,学习有利于他人的言论,去掉不善的行 为,学习有利人民的“仁人”。
墨子“劝善”一词的使用原意是教育。那么在鲁山县境内的“劝善”组织, 如“成义堂”、“劝善居”、“劝善台”等,都是以劝导人们行善事、用善言、做善 事的。
《墨子·尚同》下篇中:“善人”用语已出现,“若苟明于民之善非也,则得 善人而赏之,得暴人而罚之也。善人赏而暴人罚,则国必治。上之为政也,不得 下之情,则是不得善人而赏之,不得暴人而罚之。善人不赏而暴人不罚,为政若 此,国家必乱。故赏罚不得下之情,而不可不察者也。”
以此可以看出墨子这里讲的“善人”是“贤良之人”,是他认为有德行的“仁 人”,是值得大家效仿的榜样。所以,鲁山地方上原来的“成义堂”、“劝善居” 的讲师被称为“善人”,是当之无愧的,是人们对传道劝善者的尊称。
纵观墨子的教育思想,利他主义——“有力以助人,有财以分人,有道者 以教人”来全面分析,可以清楚第看出:墨子在教育方面,他是强有力地从事了 人生态度的延伸,要强教强学。在教育内容和目的上,墨子也十分重视德育的培 养。他培养弟子的标准是:“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的“贤良之士” (《尚贤》上)。在教育原则上他很重视理论联系实际,要求弟子们言行一致。如 在《贵义》篇中说:“手足口鼻耳,从事于义。”《公孟》篇又说:“口言之,身必 行之。”
据走访调查,鲁山境内的墨家组织中的教育都是严格的,并且说到做到。如 瀼河乡佘沟村李小旦在世时,是墨家后学“成义堂”的一个成员。人们都称他为 “李善人”。他不光在讲经劝善时诵说《墨经》,在平时也与人为善,扶贫解困。 据当事人郑光荣、杜建荣、苏庆伦等人的回忆说:每年春荒之季,李善人都拿出 自家部分口粮来接济穷人,特别是 1941 年荒灾,他自己十多亩红薯只刨了十多 担,够自家吃后,其余的让给居近的人们了。
经过对《墨子》原本的反复阅读和下乡时留意走访,总觉有一种隐约可见的 主线贯穿于《墨子》原著和鲁山境内“劝善”组织之间,总觉得它们两者之间有 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内在潜伏血脉流动,究竟是墨家后人对《墨子》文献的继 续传授,还是墨学遗风在鲁山残留,我想,应该是墨学遗风的残留。
作品来源:鲁山文学艺术网